
400-123-4567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臣,字彬斯,江苏无锡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儒家学者、教育家、香港新亚书院院士。创始人。与吕思勉、陈渊、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评选的“近代四史学家”。
回望海边,还记得风吹过水面的情景。
楚三户求容难。詹天曾说,秦已十年。
江中正心依旧,壁上藏经焕然一新。
我惭愧当时弘法的初衷,但只给长春发了一条短信。
8月31日半夜一点,我睡着后突然接到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钱斌四爷去世的消息,我震惊不已,心中感慨万千。我立即给钱家打电话,但钱太太不在家,电话也无人接听。所以我仍然不知道钱先生去世的细节(我一直这么称呼他,我仍然只能用这三个字来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感情)。不过,我接到不少于四次来自台北记者的电话。五起案件,他们都说他是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突然去世的。这正是中国人常说的“无病而死”。这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7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我第一时间来到钱先生的新家,向他问好。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在纸上流下了眼泪。
这十几年来,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大多数时候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但有时我只是路过。每次去台北,无论日程多忙,我都必须去拜访一下钱先生。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殊的,因为它是在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已经很难用“师生”二字来形容其内容了。但这两三年来,我确实感觉到钱先生的精神每况愈下。今年7月初的一次,我再也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但他的身体状况,至少表面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他的突然去世还是让我很难接受。

▲ 钱穆先生曾经做过的专题,点击图片浏览
我对钱先生的怀念绝不能用一两次、甚至三五次正式的“逝世纪念”来表达,也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的感情。对老人的尊重和爱护。所以现在我会回忆一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几个瞬间,留下我们四十年师生友谊的一些最真实的见证,同时我也会简短地表达一下此时此刻的悲伤。今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的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活,但这只能在我的情绪完全平静下来之后才能做到。
我上面引用的那首诗。这是我五年前为祝贺钱先生九十寿辰而写的四首诗中的最后一首。讲述了我们在香港的时光。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50年春天,当时我刚从北京到达香港。当时我正在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我第一次从北京来香港时,我以为这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但到了香港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让我跟钱先生学习。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雅的那次。
虽然钱先生在中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我也很早就读过他的《国史纲要》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查阅过《先秦诸子年鉴》。 ”在燕达图书馆。 ”,但他在香港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成立,学生总数不超过20人,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难民儿童。桂林街的新亚九龙时代连“大学”都没有规模,图书馆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办公室只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桌子占据了整个空间。我们在长桌一侧坐下后,钱先生走了出来。

“新亚书院”旧貌
我父亲和他见过面。他们开始寒暄一番。钱老师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学到新亚,就询问了我以前的学习情况。他表示,新亚只是一家刚起步的初创企业。即使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我也会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但我必须通过考试,而且我必须在第二天参加考试。我去考试的时候,钱老师亲自出来主持,但是他没有给我出题。他只要求我用中英文写一篇关于我的学习经历和愿望的文章。交卷后,钱老师不仅当场看我的语文试卷。试卷,然后看我的英语试卷。这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我知道钱先生完全是靠自学取得成功的,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能听懂英语呢?我忍不住想知道。
许多年后,我得知他在写完《国史纲要》后,自学了一年多的英语,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批完试卷后,钱老师笑了,我被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二学期录取为大二学生。这就是我成为他学生的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虽然钱先生的弟子遍布天下,但从口试、出题、笔试、评分到录取,也许只有我一个人包办。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虽然个子小,但很平静,很有活力,尤其是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仿佛照亮了你的心。同时,也给人一种很严肃、不苟言笑的人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但过了一两年我才发现了错误。
当时新亚的学生很少,水平参差不齐。我没有中国文化基础,比我差的人还有很多。所以,钱老师教课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要尽力去适应学生的水平。我相信他在新亚的教学是无法与他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时相比的。我个人主要在课堂之外向他学习。他给我的严肃印象使我一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雅的师生人数很少,所以经常聚会,就像一个大家庭,渐渐地师生之间也熟悉了。我们熟悉后,我偶尔会去他的房间问他一些问题。我这才知道,他真是“温文尔雅”的典范。后来我父亲还在新亚洲教授西方历史。他和我们一家人经常去太平山或石澳海边的茶馆里坐坐,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上面引用的那首诗就是这么说的。 “我还记得风吹过的水面上的鳞片”。那时,钱先生偶尔对下围棋感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实力相当。有时候,他会要求我在一场比赛中指导几位选手,就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一样。
这样一来,我对钱先生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感情非常深厚的人。但他毕竟有儒家的品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绪没有完全控制住。那时我们一家人邀请他一起看电影。这是一部关于亲子爱情的电影。演出结束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湿润了。不用说,他不仅受到剧情的影响,他也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惦记着留在中国大陆的孩子们。但这只会增加我对他的钦佩。有一年暑假,香港酷热难耐,他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他独自躺在空教室的地板上恢复体力。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他。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文集。我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本。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板上。新亚书院似乎空无一人。

钱穆先生
我和钱先生认识之后,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无话不谈。我们甚至偶尔也会有一些幽默的时刻。但他的尊严却始终存在,让你一刻也无法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也不是知识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但这是一种经过人文教育渗透的自然。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话里所说的“道尊”,或者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这种尊严让你在他面前的言行始终保持一定的分寸感,但又不会感到受到任何权威的限制。说实话,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吃饭也困难。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他怎么能算“权威”呢?这与新雅得到雅礼协会帮助后,特别是新雅加入中文大学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是患难之交。后来,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支持新亚,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的地位无疑是直线上升。上升。但就个人经历而言,钱先生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新雅开发后,搬到了嘉陵边路。
我仍然时不时去他的房间聊天,但经常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访客。有一次,刚好跟着他的一位文史学前辈也在场。突然,这位先生背诵了一篇长文。我没听懂那是什么。钱先生笑得有些尴尬。原来,他念的就是钱。王先生几十年前在北京图书馆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一切与钱先生本人无关。 1960年春,钱先生赴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两次去看望他,他和钱夫人也两次来剑桥做客。离开之前,他们和我们一家人在湖边的小木屋里住了几天。我们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将,然后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那种社交活动。钱先生还是那么自然,那么直率,那么富有感情,但依然带着那份令人尊敬的尊严。

余英时先生
我想大多数人对于上面所描述的钱先生的一生都不是很清楚。我能比较完整地看到这一面,是因为特殊的机缘。钱先生从来不懂得炒作,对世俗的名声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什么“塑造社会形象”、“建立人气”。这些“新文化”一直与他绝缘,所以他在初次与人见面时不会刻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愿意在年轻人面前说得太过溢美之辞。除非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有这样的机会,否则钱先生的真实身份并不容易被其他人发现。他深信《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惑”的一句话,接近于坚持。我不知道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我聊天时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在向我说教,而只是触及它。
如上所述,我从钱先生那里得到的教诲主要是在课堂之外。这也与外部关系有关。我只在新亚书院学习了两年半。那是新亚书院最困难的时期,钱先生经常要四处奔走。往返香港和台北筹集资金。 1950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逗留了大约两三个月。看来1951年春天,他还没有开课。 1951年冬,他再次前往台北,不久在联合国男女同性恋协会演讲时发生礼堂倒塌事件。钱先生头部受伤流血,昏迷了两三天,差点就死了,所以1952年春天他就一直呆在台湾疗养。 1952年初夏,新亚书院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我是三位毕业生之一,但钱先生尚未康复,无法返回香港参加。所以我只上了钱老师的课一年半。事实上,在钱先生伤愈回港后,也就是我毕业后,我就有机会向他请教更多私人意见。
大概是1950年秋开学不久,为了更深入地读《国史纲要》,我费尽心思地做了一个神秘的总结,摘录了书中的精华,供自己参考。我写了几篇文章后,寄给钱先生审阅,希望得到他的指点。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寻求建议。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记这样的笔记的时间也是一种训练,但你的笔记本最好留一半页空白。以后读别人的历史著作,有不同的看法时,可以在空白页上写下以进行澄清。”他不经意的一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启发,也透露出了他自己的学习态度。
《国史纲要》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观点,而是充分承认别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论证,初学者应该注意这些差异并追求你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来说,钱先生的体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在《国史纲要》的“引言”和“书序”中也隐隐约约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但对我来说,毕竟不如面对面指导、简单地给单那么亲切。伟.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小心翼翼,不随波逐流,克制自己不去看别人的作品——尤其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并尽量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思想。他的论点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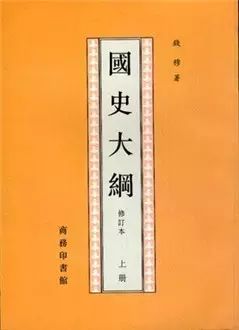
▲点击图片直接购买
《国史纲要》

撰文:钱穆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
此后,我多次在《国史纲要》中提出具体结论,并请他解释为什么说这个不说那个——每次都是我“小推”,他“大评” 。我渐渐明白,他多年来在北大等学校讲授中国通史期间,通读了同时代史学专家对一切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文本,然后根据自己的观点判断异同。对一般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有一次我们讨论西魏的军事制度时,他向我解释了他和陈寅午观点的异同。他认为陈寅午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军事制度建立中的作用,而宁愿关注胡汉势力的兴衰。他高度赞扬陈寅午的贡献,但认为专题研究的具体结论与通史所要求的综合结论可能无法完全融合。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国史纲要》读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是用心如金,语言丰富有内涵。其背后不仅有正史、九通等老史料,还有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我们讨论的范围几乎包罗万象,但重点始终是现代史学的演变。从他的讨论中,我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有自己的分类和演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视角。这是“专”与“泛”之间的一个大问题。然而,这一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专业化趋势的接触,却给如何沟通和融合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果单纯按照西方的分类,各自选择一个专门的范围来进行窄而深的断代,暂时还不能解决。研究当然会产生结果。但在熟悉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感觉牵强、无力。如果我们过于注重“常识”的传统,先有整体了解再走专家之路,其实研究者的时间、精力、智力都不允许。
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用通识驾驭专业”的道路。如今,大家都把他视为一位学术思想史家。事实上,他在制度史、历史地理学、甚至社会经济史等各个方面都下了功夫,并撰写了专门的著作。 《国史纲要》中的“南北经济文化转移”三章尤为精辟,展现了多方面的历史功绩和现代视野。我认识的在钱先生手下工作过的人中,严庚旺首先研究政治制度史,然后研究人文地理学。他们都受到了钱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953年,钱先生获得亚洲基金会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用一间楼层成立研究所,这就是新亚洲研究所的前身。当时研究生只有三四个人,我也在其中。但我当时的兴趣是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钱先生是我的导师。钱先生仍然一再叮嘱我,希望我不要过分注重年代而忽视了联系,更不要把社会经济史搞得太狭隘,不能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相协调:这是仍然有“泛化”和“专化”之分,但钱先生的路并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这个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也坦言,这个问题可能无法一刀切地解决,只能根据每个人的人性分别进行探索。
前不久我做的颜耕网特刊
也许当新的研究传统真正形成时,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这显示了钱先生治学的另一面:他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学者,承认历史的多样性,但同时又很固执,坚持走自己的路。他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采用多种观点。但学术价值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并不完全由当代人的评价来决定。说到底,时间公公还是公平的。因此,他在谈话中总是强调学者不要太急于出卖自己,导致时代潮流将他们扫走,变成吸尘器里的灰尘。这又回到了“人不知其所不知”的老话题,但他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制定了客观标准,但可惜被破坏了。战争至今尚未恢复。
钱先生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变迁的回忆也很吸引我。起初,我只是出于好奇,向他询问了各派的性格、学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民国学术思想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部分知识是书本上找不到的。民国十九年钱先生到达北平后,看似进入了中国史学的主流,但他的真实立场却与主流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并不相符。因此,他与反主流学者的关系比较融洽,甚至还有不少左翼学者可以与他交谈。比如杜寿苏就非常欣赏他,范文澜也非常关注他的作品。 20世纪40年代中期,范文澜开始编撰《中国通史纲目》,其内容很大程度上以《国史纲要》为蓝本,但解读有所不同。
此外,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南方史学家苗凤林、张琪等也与他有密切的交往。钱先生不属于任何派系,这让他更能看清各个派系的利弊;他也有自己的主见,所以他的判断清晰而有趣。 1971年以后,每次去台北见他,每当话题转到这方面,他总喜欢回忆起这些学术轶事。我曾多次请他写下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或许是他后来决定写《师友杂记》的原因。但《杂记》的文笔还是太干净、太微妙了。这是他一贯的风格。然而,如果读者没有相当的背景知识,可能很难理解他的意思,更不用说他的意思了。

▲点击图片直接购买
《师友杂记》
撰文:钱穆
版本: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
收到钱先生去世消息的几十个小时里,我在香港流亡五年的经历无数次在我脑海中重温。一些隐藏已久的记忆,现在又被唤醒了。正如钱先生所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我在本文中对钱先生的记忆主要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因为这几年是我个人人生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没有遇见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意味着:五年来,钱先生的生活已经走进了我的生活,对塑造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反之则不然,因为钱先生的人生早已定型,我对他的人生史没有任何影响力。我最多就像雪泥里的利爪,只留下浅浅的痕迹。
这篇文字是在情绪波动中写下的,我没有时间修改,也修改不了,但记录的只是一个提纲。在结束之前,我先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我在美国教学和研究已有三十年了。钱先生的作品当然与我的作品密不可分。在我的朋友和学生中,当然有很多人因为我的指导而仔细阅读了钱先生的作品。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杰里·丹纳林(Jerry Dennerline)。 《钱穆与七坊桥的世界》前年(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是根据《父母八十年》译注的专着。

然而,这三十年来,我却没有利用任何机会来宣传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好像我想创建一个“学派”一样。这也是基于钱先生的精神。俗话说“催苗促长,有害无利”。而且,钱先生一生所发挥的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过分强调或凸显他的个人角色并不是要抬高或放大他,而是要降低或贬低他。这也是他为何在张学诚“公开表态”、“谢名”的深旨上来来回回。
我个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机会直接写钱先生,因为我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涉及近现代的人物和思想。一年多前,我接受瑞典诺贝尔委员会邀请,参加今年9月初在世界各国举办的讨论“民族历史观”的学术会议。我想借此机会听听其他国家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所以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参加。我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历史观念的变迁》。论文本来是6月底交的,但因为7月初回台北开会等事情,就推迟到了最近。本文从张秉霖、梁启超开始,最后的代表人物恰好是钱先生。在收到钱先生去世消息的前几个小时,我正在写《国史纲要》所体现的国史意识。也许他去世的那一刻,就是我介绍《国史纲要》的时刻。这里面有什么归纳的理由吗?或许,正如我上面所说,由于他早年对我的塑造力,这种力量在他去世前就在我的潜意识中涌出。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但更让我难过的是,我必须对这篇文章进行最后的修改,添加他的去世年份,并将动词改为过去时。
钱先生走了,但他真正的精神和真正的生活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继续在无数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中,包括我这样的平凡生活。
(本文写于1990年)

《余英时文集:近代学者学者》
余英石 撰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本文最初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英时文集:近代学者学术》。编辑:一一。其他公众号或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您的朋友圈。
▼
点击关键词即可查看往期精彩片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点击图片
购买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定制版《阿城文集》~